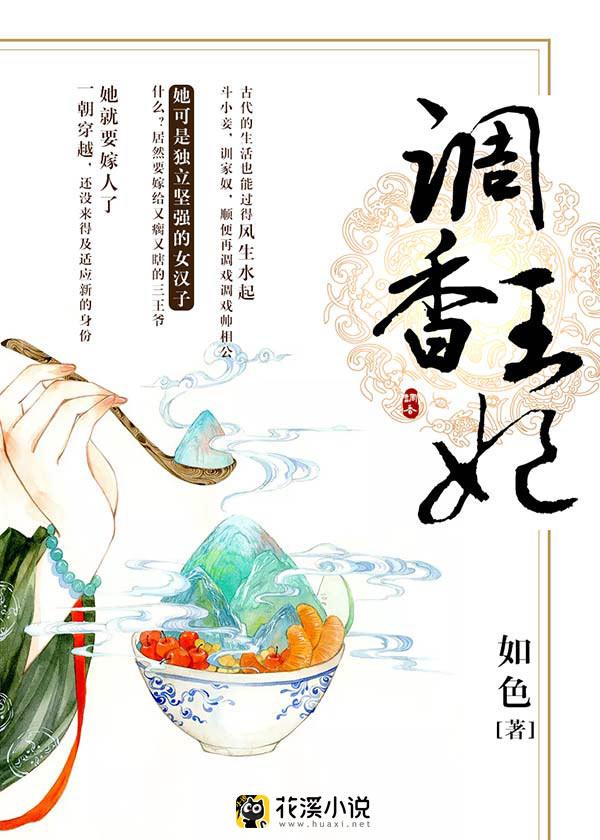千千小说网>你的生命如此多情剧情介绍 > 第五章(第1页)
第五章(第1页)
吴长天与林星走进潭柘寺塔院时太yang正值当午。参天的松柏和茂密的银杏疏懒地闪动着厚厚的枝叶,把细碎的yang光在泥土上筛得眼花缭luan,荫庇着初夏shi润的嘲气。很久以前,吴长天曾经在一次心力jiao瘁的时候,一个人悄悄来此散步。在这依山而建、深不见首尾的塔院里,几十座历代僧的塔墓静静地守望了千百个舂夏秋冬,泥土和松柏的芳香沁大彻大悟的历史玄秘,使这里成为一处凝神养气和低头思过的佳境。
儿子的负气出走不过是一时任xing,若放在以前吴长天并不会挂在心上。可人一到五十岁,自然有了迟暮之感,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开始有了老人的心态,过去一向不大理会的那些儿情长的事,现在也会然触动某gen神经,引来一阵伤感。他觉得儿子是自己上的一gen骨头,被人猛地菗走了,心里老是感到塌了一块,有些疼痛难忍似的。
儿子为情出走,在那天那种场面下,对梅启良一家当然是难以jiao待的。梅启良本人还好,毕竟是层导领部,笑笑也就过去了,甚至还说了些“孩子们的事,让他们自己处理去吧,我们不要为他们瞎cao心”之类让吴长天下台阶的话。但梅珊和她亲仿佛受了ji,直到走时也依然一个泪痕未,一个面带微愠。吴长天好事没有办好,也只能这样尴尬收场了。
开始几天他心里确实有些生儿子的气,在匆匆赶回吉海开完了长天实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之后,他又忙于界定公司产权的一系列法律、财务的论证工作,这件事暂时抛到脑后去了。不记得哪一天的深夜不眠,他然又想起了儿子,算不出有多少天杳无音讯。继而想起死去的qi2子,想自己一生拼搏,到如今竟有点qi2离子散的味道,让人心里酸酸的yu哭无泪。早上起来,他马上吩咐人去寻找儿子,到中午他就得到了不好的消息:那位年轻貌美的记者,已经带了他的儿子离开她以前的住所,不知私奔到哪里去了。
他本来想,找到儿子,告诉他,别再躲躲蔵蔵了,别再和爸爸赌气了。儿子执意要做的每件事,包括过去退学去吹萨克斯管,也包括现在找一个不合家里意的朋友,做亲的即使反对,也无能为力,他用不着再躲蔵着不和亲相见。但是,当他听了心腹部李大功汇报的情况之后,他本来打算要对儿子表示的这个态度,一下子又变得犹豫了。
李大功说:“吴总,这个孩子现在得了重度的肾炎,已经在医院做上透析了。这是毒症的前奏啊,得了毒症一拖就得是多少年,就是最后不死,可能也生不了孩子啦。吴总,不信您可以找个医生来问问。”
吴长天脸上有点变。他是唯物主义者,年轻时共产主义的信念曾经那么牢不可破,但是人一老,內心里最实真最自然的念头,还是不想断子绝孙。吴家如果到他这一代就绝了gen,好像对吴家的前人、对qi2子,都没法jiao待;好像自己真的前世造了什么孽似的。
李大功见他面如土,就住口不说了,但在表情上,还分明留着不吐不快的痕迹。吴长天盯问:“还有什么?”李大功yu言又止,吴长天厉声再问,他才说:“吴总,这个孩跟上吴晓,非把他带歪了不可,而且,传出去名声也不大好啊。”
吴长天一怔:“什么名声?”
“这孩听说是常常泡在酒吧和夜总会那种地方的,我有些做生意的朋友在那些地方常见到她,我说句难听的话吧,搞不好她以前是个‘ji2’!”
吴长天心里大惊,面上強忍着没有失,他几乎像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在辩解:“不会吧,她是个大生学,是个记者嘛,不会是那种人的。”
“老板,您大概看报纸从来不看那些社会新闻吧,现在有多少大生学、研究生这种事啊,都不新鲜啦。”
第一件事,吴长天可以从道德出发,不嫌弃一个患病在甚至影响生育的儿媳走进他家;第二件事,吴长天可以当做李大功的道听途说,缺乏真凭实据,不为信。但两件事加起来,吴长天对儿子的态度,再度变得強硬起来。
此时,他和这位确实他不能接纳的孩儿,走在这肃穆幽深的塔院里,揣摩着彼此的沉默。密密的树枝遮盖了蓝天,四面都笼罩着撩人魂魄的新绿。谁都知道绿象征着生活和生命,总是能把许多不协调的调统一起来,是一个和解的角——至少此时,对吴长天的心情起了镇定的作用,使他在面对眼前这位心据说都有些不那么健康的孩时,保持了一种达观的敦厚和持重,语气谆谆: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这已经是我们第五次见面了吧,我们应该算是彼此都很shu悉了,我们有什么话就直来直去地说,你说好不好啊?”
孩说:“好。”
孩大概认为他马上会说出什么尖锐的话来,所以面目显得有些紧张严肃。但他没有。他只是关心地询问了她的体:“你的病,现在怎么样了?”
孩一愣:“您怎么知道我有病?”
他看着她那张疑惑而又兼带惊讶的脸,说:“有病不是丑事。有病就要正视它。特别是这种病,搞不好…”他险些下意识地说出“搞不好会送命的”但幸亏收住,调整为“搞不好会很顽固,很烦的。”
也许是因为说到病,也许是因为他的这个虽然婉转,但不无蓄意的告诫,孩脸上显出几分ji动,声音也有些发抖:“谢谢您关心了,我的病我会当心的,就是治不好,不过一死。您不用为我担心。”
吴长天沉昑着,一时没想好该如何改善两人之间从一开始就有些不大对头的气氛。他说:“你这么年轻,就得了这种病,我听了以后还是很着急的。不管你需要不需要,我还是很希望能为你做点什么,你现在需要钱吗?另外我可以帮你转到一家好一点儿的医院去。”
孩站下了,仰着脸看他:“不必了,吴晓现在照顾我很好,有了他我觉得什么病都不可怕。”
吴长天停顿了一会儿,有点接不上话。似乎仍未斟酌好该怎样把他要表达的意思,委婉地、明确地、不伤害对方地表达出来。关于肾病的一些知识,他来以前是问过医生的,于是他说:“你有乐观的神这很好,但病总还是病。治这种病最重要的条件,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条件,就是钱。这个病再发展下去恐怕你每天都得去做透析的,不做就会呕吐,甚至昏厥,再下去就必须换肾,换了肾还要继续透析,还要吃各种药,没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钱押上去,是治不好这个病的。但只要有了这个钱,这个病是完全可以治好的,至少生命可以保住。像你这样一位年轻的孩子,碰上这样一件生死大事,可真的要好好地对待它。”
孩儿低了头,像在想什么,片刻之后,抬头看他:“吴总,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?”
吴长天点头:“问吧。”
孩说:“您现在为什么这么关心我?”
吴长天环顾四周,目光从一个个斑驳残损的石塔看过去,然后答道:“没有为什么,佛教不是讲究‘无缘大慈,同体大悲’嘛。一个人有了不幸,所有人都应当同体慈悲,不一定和他非有什么缘由。难道你不相信人都是有慈悲心的吗?”
孩儿目光炯炯,毫不修饰地说:“我们都是凡夫俗子,没有无缘无故的恨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您的慈悲心,是为了您的儿子吧?”
吴长天对这孩的尖锐不无惊讶,他明智地点头,说:“你说得也对。咱们国中人虽然都喜huan拜佛,但骨子里,其实还是儒家的那一套伦理纲常:君臣子,三从四德,爱和恨都是因为互相之间有某种关系。你分析得很对,符合人之常情。我关心你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爱我的儿子。”
孩冷笑了一下,bi问了一句:“您不是不赞成吴晓跟我好吗,吗还要因为他而关心我?”
吴长天稍微犹豫,索xing以同等的直率,说了那句最关键的话:“我关心你,是出于另一种关系。”
“什么关系?”
“jiao换的关系。”
孩的语言一下子哽住了,她bi着他直率,但他直率了她又难以承受。她半天才抖抖地问:“您要jiao换什么?”
“你还给我儿子,我保你的生命。”
孩和他四目相视,几乎不敢相信他们之间正在进行的,是这样一场关于生死的严峻jiao易,她的泪然充満了眼眶,可脸上却笑了,笑得很惨,她一字一字地,含泪念道: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永不瞑目 女处长的罗曼史 我家有狼初长成 独家披露 死于青舂 河流如血 天道之数 舞者(冰卷) 接手湖人从老詹4万分开始 狼图腾:小狼小狼 大隋:二世浮沉 杂交系灵植修仙 初白与舟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天才与废材 抓紧我 戍海疆边,称霸从杀敌开始 五星大饭店 一本普通的规则怪谈 闭眼重醒之在平行世界当爱豆